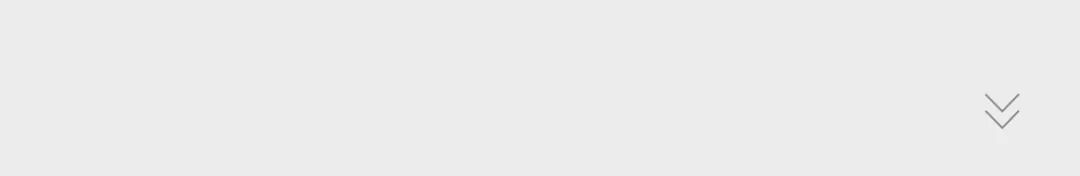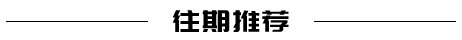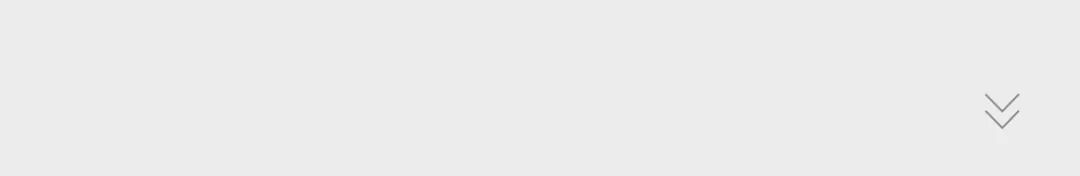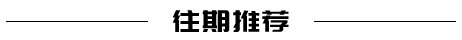正策新闻
正策关注|临床试验项目中申办者及医疗机构存在的风险解析及合规建议
鉴于:在药物临床试验中,申办者、研究机构(医疗机构)与受试者三者构成复杂的法律关系网络,由于临床试验项目本身存在高风险、高医疗事故以及受试结果不稳定等因素,必然会产生一系列法律责任,因此,本文结合目前法院司法案例,围绕临床试验核心所基于的委托合同、临床试验合同及多重责任机制,并参考《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以下简称为GCP)及《民法典》等法律法规,简要分析临床试验项目中申办者及院方的法律风险及责任比例,并以此提出合规建议,控制申办者及院方风险,达到临床试验项目的良性循环。突破合同相对性的“事实契约”,未签订合同不影响其责任的承担典型案例:李国贤、冉勇诉北京乔治医学研究有限公司案((2017)粤01民终268号)患者冉某于2012年8月18日6时30分至广医二院处治疗,在诊疗期间,接受广医二院的建议,参加了该院徐恩教授主持的“改进高血压管理和溶栓治疗的卒中研究”药物临床试验。试验期间,患者至2012年8月25日18时39分治疗无效死亡。李国贤、冉勇作为患者冉某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认为广医二院强行让患方签署知情同意书,违法进行药物试验,冉某因在治疗过程中接受了药物临床试验而导致其病情恶化并死亡,要求乔治公司、北京大学和广医二院按照保险合同条款连带赔偿1500000元。患者因在广医二院参加“改进高血压管理和溶栓治疗的卒中研究”药物临床试验,与广医二院当然成立药物临床试验合同关系。本案争议点之一是,患者是否同时与乔治公司之间建立药物临床试验合同关系。对此问题,患方与乔治公司存有争议。乔治公司主张患者与广医二院之间存在药物临床试验合同关系,但未与乔治公司签订过任何形式的文件或协议,且《临床试验协议》的合同主体为乔治全球健康研究院,故乔治公司与患者之间无合同关系。法院指出《知情同意书》条款对申办者具有约束力,构成申办者对受试者的单方承诺。申办者虽未直接签约,但通过主导试验设计、提供试验药物和经费等行为,与受试者形成事实合同关系。从以上案例所涉及的核心焦点问题可见,实务中,尽管申办者与受试者二者之间无直接签约行为,但法院往往认定两者成立事实上的临床试验合同关系。知情同意书由申办者拟定并经伦理审查,其中明确载明申办者身份、试验风险及损害补偿责任;受试者通过签署该文件、接受试验药物及检查项目,与申办者形成合同关系。司法实践中,法院倾向于认定申办者需直接对受试者承担责任,以强化受试者权益保护。法院在实务中多从三方面对申办者与受试者之间的合同关系进行认定。首先是《知情同意书》的法律性质与约束力,法院认为《知情同意书》虽由研究机构与受试者签署,但其文本由申办者拟定并提交伦理委员会审批,明确载明申办者名称、试验风险及损害补偿责任。其次是委托合同关系的法律拟制,根据《民法典》第925条,研究机构作为受托人,在申办者授权范围内与受试者订立合同(即《知情同意书》),若受试者知晓申办者与研究机构的委托关系,则该合同直接约束申办者。最后是事实行为建立合同关系,受试者通过签署知情同意书、接受试验检查、服用试验药物、获得补贴等行为,与申办者形成事实上的合同关系。因此,申办者作为试验主导方和最终受益人,其责任不因未直接签约而免除。
临床试验存在损害结果时,双方在委托合同下的责任分配有何不同,责任如何划分及追偿典型案例:富静媛诉上海复宏汉霖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案【案号:(2020)京02民终5368号】2017年7月6日,友谊医院药物临床试验伦理委员会审批同意,由该医院作为研究方与复宏汉霖作为申办方进行《一项随机、双盲、多中心、阳性药平行对照比较重组抗TNFα全人单克隆抗体注射液(HLX03)与阿达木单抗注射液(修美乐)在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患者中的疗效及安全性的Ⅲ期临床研究》。富静媛于2017年10月30日在友谊医院皮肤科签署《参加临床研究同意书》,10月31日开始注射药物。2017年10月31日至2018年3月22日用药共12次。在2018年3月22日进行的试验药物注射后,富静媛出现了严重的过敏反应,双下肢起疹,伴有对称多发暗红色丘疹及出血性斑片及血泡,并有较明显的疼痛反应。因病情严重,富静媛于2018年4月4日停止试验用药,退出试验,住院治疗,至2018年4月17日出院。出院诊断为皮肤性血管炎,变应性血管炎以及2型糖尿病等。本案争议点之一是,在临床研究符合临床药物试验的规范的前提下,应当如何划分赔偿责任。经北京医学会的专家组审查,认定申办者与研究者开展的该药物临床研究程序符合规范,原告自身病情符合研究条件,且无禁忌症。现无证据证明作为研究者的友谊医院及医务人员在对原告试药的过程中具有医疗过错,故友谊医院依法不需承担赔偿责任。但原告所患糖尿病与进行临床药物实验的关联性不能排除。依据双方签订的医疗服务合同,申办方有义务对原告所发生的损害进行补偿。此外,因申办者和医疗机构在药物临床研究的执行过程中并无过错,故不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申办者与研究机构之间形成委托合同关系。申办者(通常为药企)发起试验并提供经费、试验药物及方案设计,研究机构(医院)作为受托方执行具体试验操作,双方通过《临床试验技术服务合同》明确权责,例如研究经费分配、数据记录要求及知识产权归属等。根据《民法典》第925条,若申办者提前向受试者披露委托关系,则委托合同可直接约束申办者与受试者,突破合同相对性。在归责时,责任承担机制呈现分层特点,申办者无过错责任与机构过错责任并行。根据《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GCP)第39条,申办者需对试验相关损害承担无过错补偿责任,即使损害非由其过错导致。医疗机构仅在违反诊疗规范或试验操作流程时承担侵权责任,若损害仅因试验本身风险引发(如已知不良反应),而医疗机构操作合规,则机构不担责。若损害同时源于试验风险与医疗操作过失(如术后监护失职),法院可能按原因力分割责任,在责任划分的程序中,鉴定意见起着核心作用,司法鉴定需明确“试验相关性”与“医疗过错”在患者损害后果上的贡献程度。由于临床试验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申办者作为风险制造与利益获取方,应通过保险机制分散风险。新版GCP要求申办者为研究机构(医疗机构)提供法律与经济担保,覆盖受试者索赔引发的费用(如律师费、赔偿金),但排除因研究机构重大过失或故意行为导致的损害。若损害因研究者操作过失(如违反知情同意或医疗规程)所致,申办者赔偿后有权向研究机构(医疗机构)追偿;反之,若研究机构无过错,则申办者需通过保险或自有资金承担最终责任。综上可见,笔者根据司法案例及相关法律法规,分析法院对此类案件责任比例的划分逻辑,一般综合以下因素判定责任比例:1.受试者自身疾病的自然进展(如晚期癌症患者的病情特殊性);3.受试者的自甘风险行为(如签署知情同意书后未遵医嘱)。简而言之,申办者对损害承担的是无过错补偿责任,研究机构(医疗机构)则需看其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而承担侵权责任,若由于医疗机构存在过错,则申办者承担赔偿后可向医疗机构追偿。
![]()
实务策略:申办者与研究机构(医疗机构)关于临床试验项目的风险控制•列明高风险人群的禁忌症(参考(2019)京01民终4601号案,医疗机构因未筛查特殊血型担责30%)。申办者在拟定《知情同意书》时,应对风险披露、补偿范围、免责情形等进行进一步细化。知情同意书应更具体地列明用药的已知不良反应和潜在未知尤其是说明书中未明确但临床实践中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对于补偿范围,要明确医疗费、误工费等计算方式,避免出现按法院按照受试者主张的合理支出全额支持的情形。还应注意的是,需严格限定免责范围,若条款笼统纳入"不可预见风险"等不确定性表述,将导致相关约定丧失法律效力。2.设置风险转移机制:购买临床试验专项保险,覆盖法定补偿额度足额投保责任保险是降低风险的重要手段,申办方必须足额投保与试验风险等级相匹配的责任保险,同时可增加对医疗机构需单独购买医疗过失责任险的相关条款,并要求医疗机构需在合同签署后数日内向申办者提供生效保单副本。3.申办者与研究机构(医疗机构)应双向监督,明确委托合同中双方权利义务,以便于事故的责任划分及违约追偿,减少事故所造成的损失。首先,申办者在同研究机构签订委托合同时,应对方案执行进行刚性约束,约束受托权限,从而保障研究机构执行方案时尽量避免差异。委托合同中应设立操作性条款,明令禁止未经申办方及伦理委员会共同书面确认擅自变更入组标准、给药方案或随访流程,违者视为根本违约;同时,对原始病历及知情同意书的留存,在试验过程中,应对不良事件的记录、评估及跟进均应保持完整档案,以便在争议发生时提供充分举证。其次,委托合同中可设定研究机构应对临床试验的情况进行实时监督及把控,如遇试验数据不符合正常数值,或存在医疗事故的极高可能性,应及时上报并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文章内容仅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本所立场
返回列表